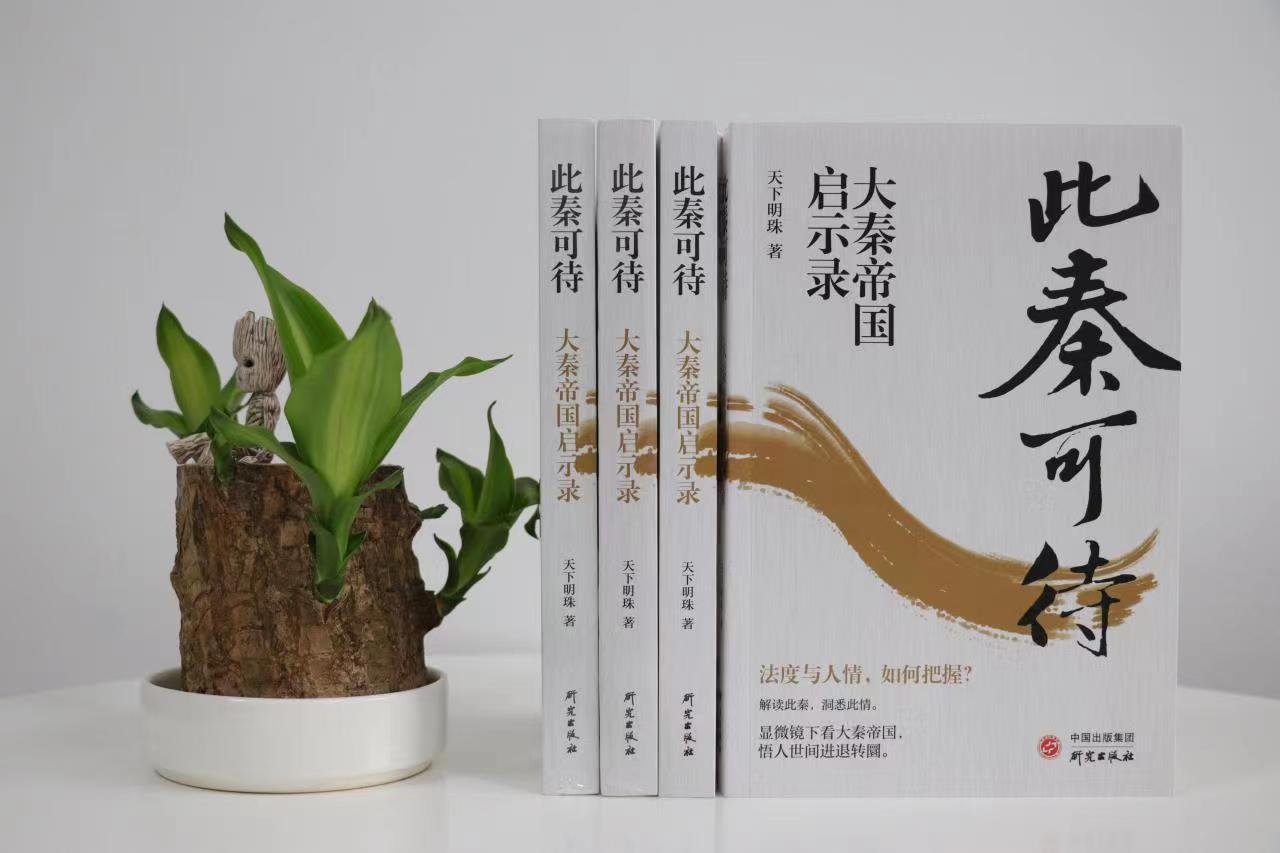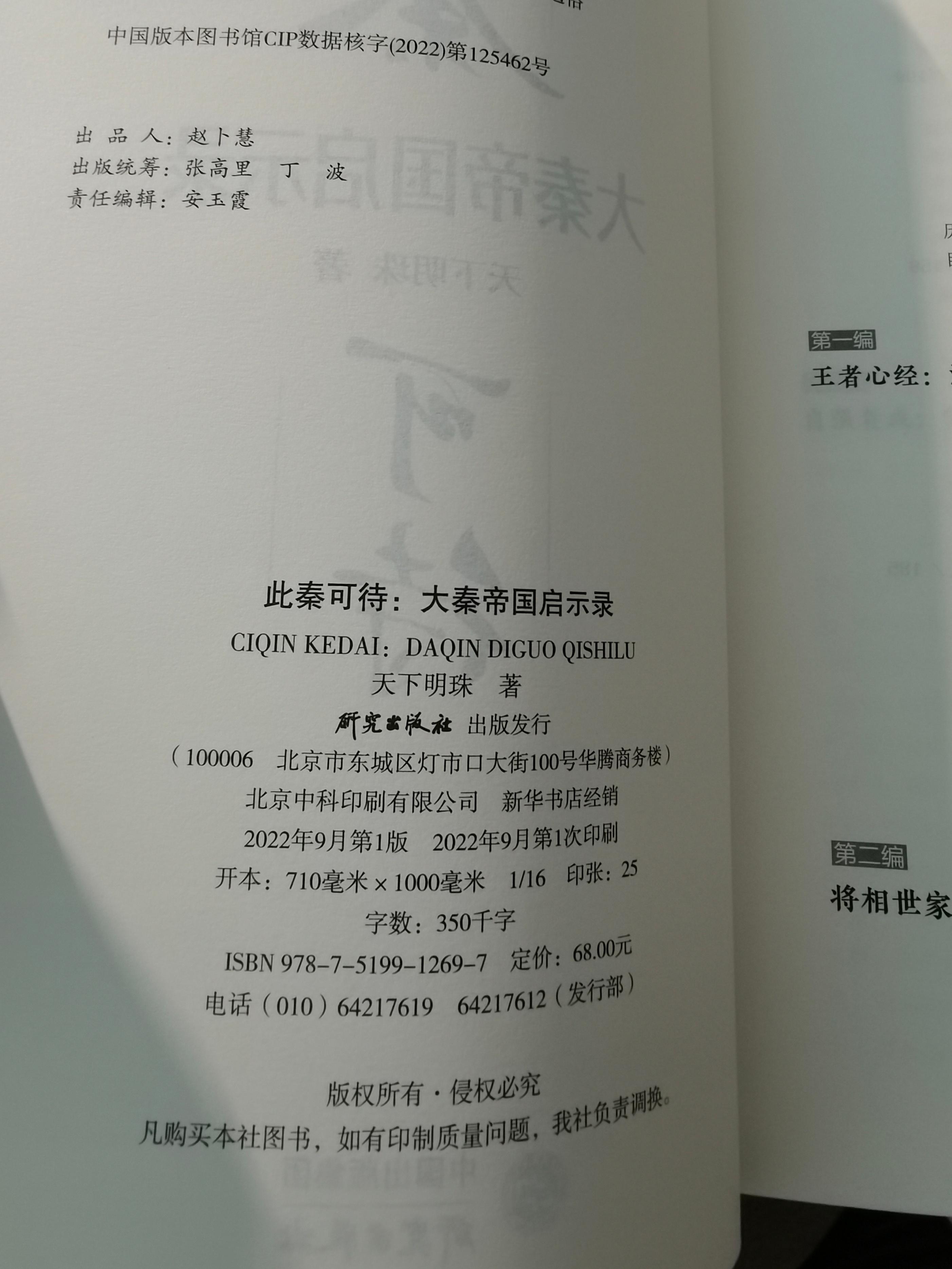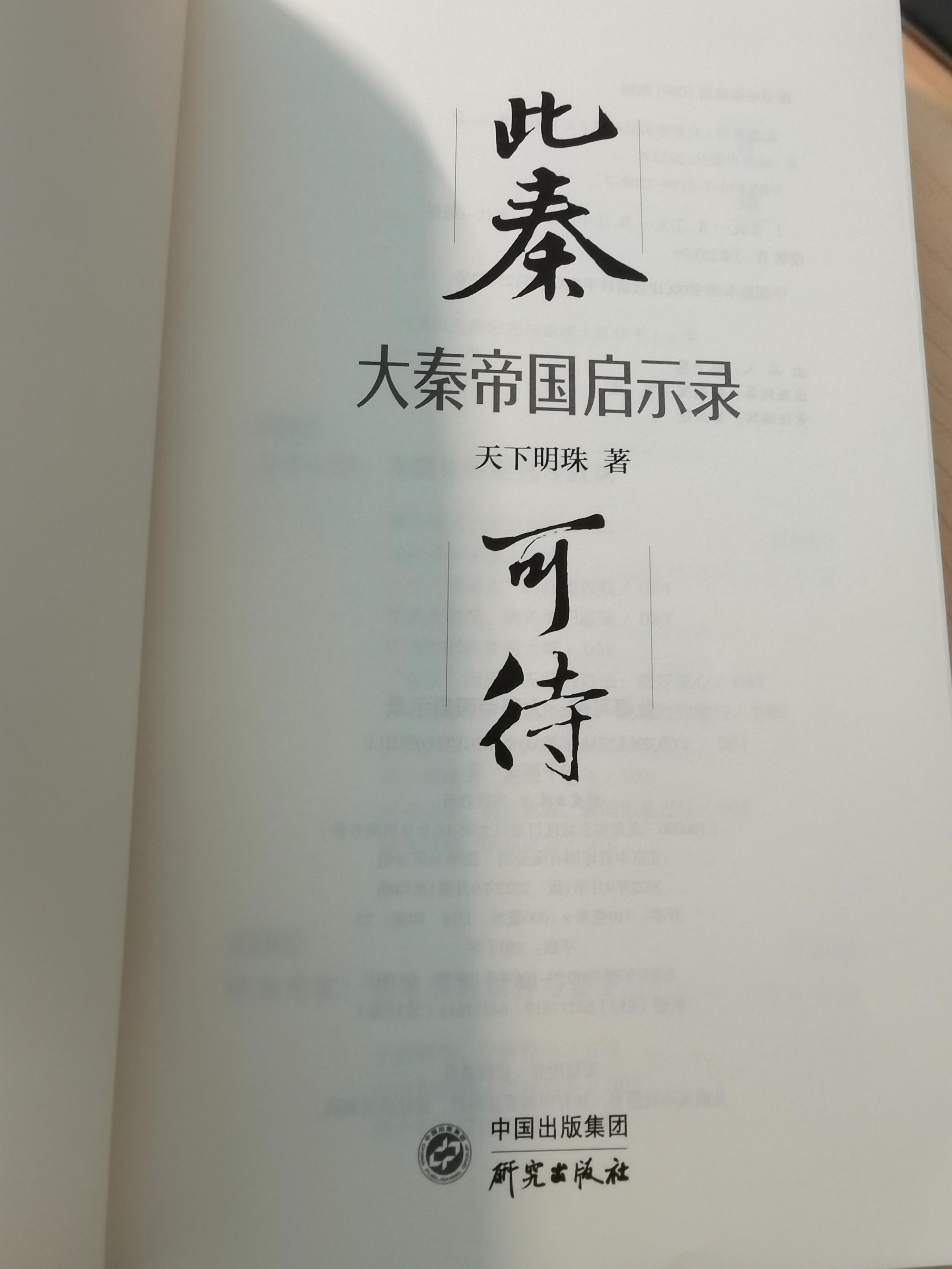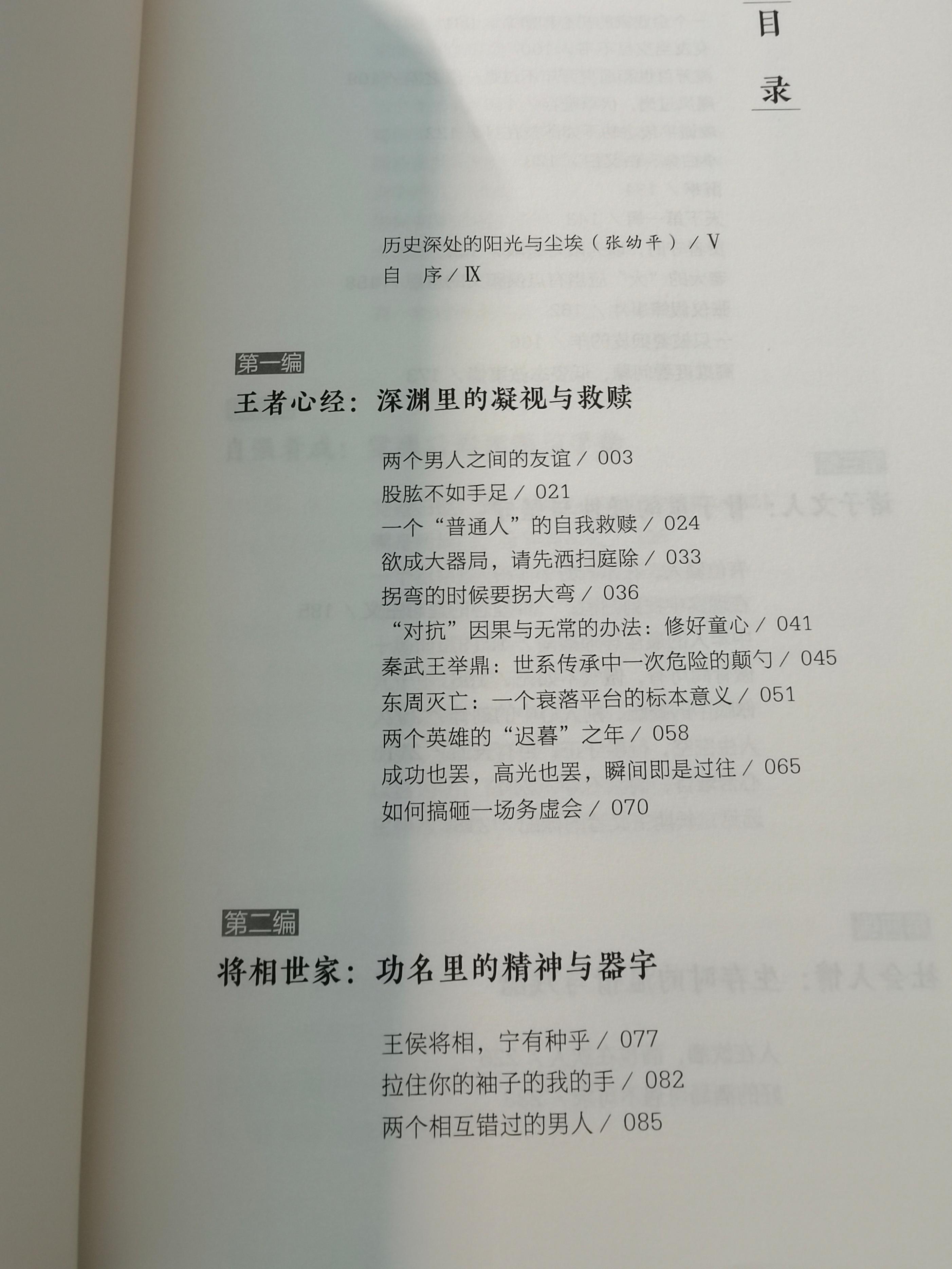太子摩托车转弯技巧(秦孝公和商鞅之间的区别)
一
成熟就是既憋得住尿,又憋得住话。放眼人的一生,这样的日子似乎并不长,这是一顿美餐中最舒服的一道,这是一天中阳光照在身上最舒服的时刻。倘若能长期地做到憋得住
一
成熟就是既憋得住尿,又憋得住话。放眼人的一生,这样的日子似乎并不长,这是一顿美餐中最舒服的一道,这是一天中阳光照在身上最舒服的时刻。倘若能长期地做到憋得住,最终能不憋而住,则可渐渐养成一种叫“沉稳”的气质。
我们要品尝人生醇厚的味道,不可没有这一气质。
商鞅变法以商鞅为名,其实也可称为“秦孝公变法”。秦孝公在变法之中的作用非同寻常、不可或缺。他为行变法所做的种种准备、铺垫,可谓思虑深远,其中表现出来的沉稳气质令人折服,其父选其为继承人而非嬴虔,不可不谓眼光老辣。
秦孝公和商鞅要做的这件事,注定会有很多保守势力跳出来反对,区别只在于时间早晚和激烈程度。商鞅是笃定要执行的,十条法令分两次实行,已经是他的“圆通”之处了,朝局的运筹帷幄既不是他所能为,也不是他能想。如果说他是杰出的管理者,那么秦孝公就是杰出的领导者。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领导力,这是一种把握全局、综合运用资源的能力。
秦孝公这个年轻的老司机开着老秦这辆车打算拐弯的时候,总的指导原则是尽最大可能让保守势力晚一点跳出来、跳得少激烈一点。
如果你去采访他,他很可能会沉吟片刻,然后告诉你:
“年轻人,拐弯的时候要拐大弯。”
二
拐弯的时候要拐大弯。因为拐得太急容易翻车。
让我们来看看秦孝公是怎么拐大弯的吧。
从时间上看,秦孝公拖得很长,着急的事慢慢做,他理解得很透。他和商鞅长谈三昼夜之后,甘龙、公孙贾、孟西白家族或多或少有点紧张,但他却只是封了商鞅为客卿,没有公布什么方针或措施,之后三个月都没什么动静,直到开春启耕大典之后才正式启动变法。这期间他所做的,概括地讲,是“疏导”,而且是“不着痕迹的疏导”。
从手法上看,他把权力先从甘龙等人身上转移到嬴虔,再从嬴虔身上转移到商鞅。也可以说,他先把权力从上大夫等职位转移到左庶长这个职位,然后任命商鞅为左庶长。这的确是一个大弯。试想,如果直接把甘龙等人的权力转移给商鞅会怎么样?恐怕甘龙等人会受到直接的刺激而有激烈的反应吧。这就好比,张三从图书馆借了书,然后应图书馆要求归还给图书馆,你再从图书馆借到同一本书,你和张三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,也没有一毛钱的纠葛,但如果是你在图书馆办了借阅手续,图书馆要求张三把书直接给你,那么存在一种可能,张三会觉得是你太想要这本书了,导致他能借阅的时间缩短了,张三和你之间就有了至少一块钱的关系,那可是十毛钱呢!
所谓“不着痕迹”,是温水煮青蛙的另一个说法。秦孝公第一步,拜商鞅为客卿,相当于聘为顾问,这是虚的一面;同时任命招贤馆所留士人为实职,比如县令、郡守,这是实的一面。一虚一实,让人挑不出理来。
第二步,过了些日子,和嬴虔沟通好后,将上大夫甘龙升为“协理阴阳、融通天地、聚合民心”的太师,把长史公孙贾升为太子傅,左庶长嬴虔也加太子傅,中大夫杜挚升为太庙令,享受上大夫待遇,甘、公孙、杜三人原来管的“琐碎政事”交给左庶长嬴虔和内史景监。这番操作下来,甘龙等人职位虽然提高了,但权力转移到了左庶长嬴虔那儿。同时,军队方面一个不动并且还分别晋升一级,这是稳定军心。
第三步,和景监、车英商量好后,将景监由内史调动到左庶长府长史职位,卫尉车英调动为栎阳将军,都是降级使用,但又都是实职。这既给甘龙等布了个迷魂阵,让其心情愉快而精神放松,又让可靠人选掌控了枢要。
所有的这一切,商鞅一概不知,这是秦孝公“决意不让卫鞅过早地在前期疏导中显露锋芒,树敌于元老重臣”,可谓一手掌握,了然于心,胸有成竹。
第四步,冬天过去春天来了,秦孝公在启耕大典后第二天安排朝会,由商鞅以客卿身份和诸大臣对变法大政进行正面交锋和讨论,最后达成决议变法的一致意见。顺其自然地,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,主持国政、推行变法,嬴虔改任上将军,并将代表无上权力的穆公剑赐予商鞅。至此完成全部的关键权力转移。
甘龙虽然不是到了最后才明白,但也无可奈何。这就好比和一个上手在下棋,每一步都觉得被动,总想着抽出手来抢个先手,却被牵引着无法脱身。职位的名称不重要,重要的是赋予的内涵。秦孝公给予客卿很高的礼遇,包括内侍隆重报号、贵位就座等,客卿就有了很高的隐性权力。上大夫杜挚任太庙令,实际上离核心远了一层,这个上大夫就缩水了。秦孝公实在是运权的高手。
甚至朝臣巷议都是在他的意料之中,并有适当的用处:“教他们说去,吹吹风也好。”
秦孝公这个大弯转得实在是高明。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,那就是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争取甘龙,而直接给他贴上了“肯定不会真的合作”的标签,这一点让甘龙有点失望。
至于原因,秦孝公很可能是这样想的:
你支持变法也罢,不支持变法也罢,你都是要给商鞅同志让路的。
有时候,真的是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,毕竟当初太子之位未定之时,甘龙站的是嬴虔的队。
三
不管怎么说,秦孝公是用绣花针的功夫在完成这一切,确实是沉稳之极,一招一式都是稳扎稳打、步步为营。
有这样的弟弟,当哥哥的嬴虔也多了几分沉稳。虽然对新法有些不理解,但口风把得很严,对于孟西白三人的来访“绝口不提栎阳国事”,借回绝求见的宗室老少表态说“我素来不在家中见族亲和臣子”,让孟西白三人知难而退。意思是在家里绝不谈公事,公事只在办公室谈。
其实,沉稳,不乱说,是因为说了只会惹事,不能解决问题。本来是思想上、情绪上的问题,过几天想通了就好了,若是在想法尚不成熟的时候想说就说,好了,话一出口就成为“某人在某时某地说过某话”的事实,无论你将来真实的意见变化为如何,这始终是个小辫子。历史问题,常常会成为现实问题。
这一点上,秦孝公嬴渠梁也罢,前左庶长、现上将军嬴虔也罢,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。
当然,秦孝公的这一番操作,多少有一点“术”的味道,这不用为他辩解。换作商鞅,很可能做不出来。所以这两个人,真的是各有所长,相得益彰。
术,好比是工具,本身没有好坏,发挥作用的好坏取决于用的人,所以孔子说过:“君子不器。”就是说你不要拘泥于固定的程式,好像拐个大弯就是搞阴谋,你也可以说是尊重客观规律。
我们谈论秦孝公,重点不是看他这个“术”,而是注意看他的沉稳心态。他那么急于希望秦国强大,又遇到了命中的能臣,又有了基本明确的施政思路和措施,却能够沉得住气,不急于一天两天,一月两月,而一旦出手,则迅如闪电,坚定无比。我们要学的,其实是每临大事有静气,抑或是一句老话:
“静如处子,动如脱兔。”
摘自《此秦可待:大秦帝国启示录》,研究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。